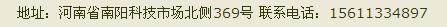神友回忆80年代的摆摊儿经历交地皮税
最近在关于“摆地摊”这一热门话题中,总能发现疫情期间的人间烟火气悄然升起。在华灯初上,在城市的视野中,聚集了许许多多摊点,用一句“人山人海”来讲述这场地摊经济,人们迫不及待的从渴望中走向内心世界共享美好生活的情怀。不难看出“小”地摊里蕴含着“大”民生。
火了的是城市的一景,活了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二会”精神以来,从上到下为活跃地摊经济,畅通市场循环,唤醒冷寂了一季的民生之事。或许你站在那里,就像茫茫人海中,回眸的那一刻,已是怦然心动。
01.第一次跟父母摆摊说起摆地摊,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父母亲承包了坐落于玻璃厂对面的原种场第一副食门市部。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素有老实厚道的一家人,摸索着做起了生意。记得承包门市部的头一年,正好四月初八赶二郎山庙会,为了多赚点钱,头一晚父母商量,由父亲一个人照看着门市部,我和母亲早早就推着平板车,去副食公司进货。主要是卖吃喝方面的,有水果糖、面包、混糖饼、月饼、汽水以及格瓦斯等;顺便带了些火柴、火香、甘字水烟、工字卷烟、青城和大雁塔烟。当时从副食公司进完货,医院(医院)给爷爷送了些日用品后,我们就推着装着杂货的车,跟着赶会的人群,来到了二郎山脚下,我眼尖,老远看见一块不是很大的空地,招呼着母亲赶紧把车推过去。母亲看了看周围,满意地说,今天运气好,这儿有树荫凉,她一边停稳平板车,一边让我找来石头、砖块把车支撑住。我和母亲开始把货摆放开来,为了防止吃的食品落上灰尘,我们在两旁的树梢上,搭起了一个布篷子。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又过来两家摆摊子的,一家是王家畔村的卖五谷杂粮,另一家是布料、衣服鞋之类的。摆好货摊,就开始张罗着开市,你别说,市开好了,一整天都顺当。看着两家人已围过来好多赶会的,我也不由自主地把纸箱子弄得更显眼,香喷喷的面包和混糖饼,总能吸引几个小馋嘴。大人小孩赶会就是出来逛一逛,再就是买一些实用的物品,尤其是小孩,他会缠着大人买这买那。这不,小馋嘴不走了,死死拽住大人的衣襟。
“多少钱一个面包,还有汽水一瓶几毛钱?”“面包一毛一,汽水二毛钱。”只见大人从上衣兜里掏出五毛钱递了过来。“买上两个面包,一瓶汽水,剩下的八分钱买成糖溜溜。”母亲把包好的面包递给小孩,我呢,不假思索地拿给六颗糖,顺手用起子把汽水打开,汽水瓶是要回收的。不一会,小孩面包下肚,汽水也底朝天了。大人则圪蹴在树荫凉一边抽烟,一边拿起火香和水烟闻着,不时说道:“味不错,是甘字水烟,包上两块水烟,一把火香。”王家畔村的摊主回应道:“人家在南郊农场开门市着呢,货真价实,我们经常去那里喝水、吃饼子。”他这么一说,我们都觉得遇上老熟人了。赶会的人越来越多,平板车上的东西也卖出不少,已是晌午,母亲给了我五毛钱,让过去买个肉馍吃,我转了一圈回来了,手里拿着两根冰棍,把剩下的四毛钱塞进母亲的口袋了。还是吃自家卖的饼子吧,再喝上一瓶格瓦斯。因为温度很高,木箱子里的格瓦斯所剩无几,刚刚买冰棍时,就看到一家卖货的,格瓦斯盖炸飞了,泡沫溢了一地。
天快擦黑时,我和母亲收拾着摊点,准备回家。那几家摊主也开始收摊,脸上都挂满了笑容。二郎山戏台依旧是唱着山西梆子,不远处的空地上电影《地道战》刚刚开始。
带着一脸的疲倦,我和母亲推着平板车回到门市部时,老远看见父亲站在门前张望着。我们一起把剩下的东西搬回去,父亲和母亲开始算账,拿出进货单,除去成本价,以及出门时带的零用钱,再把剩下的物品一清点。父亲笑着说,你们娘俩个和我今天站门市收入相差一半,走,今天早点关门,回家吃饭去。父亲推着平板车,我则坐着,星星在夜空说着悄悄话,这就是我的第一次摆摊经历。
02.独自摆摊儿做生意到了我读初中和高中那几年,家里每年都种着十几亩地,除了几亩蔬菜和西瓜,剩余的都种了玉米。每到周末或放暑假时,我都会骑着自行车驮着一箱西红柿或豆角等蔬菜,车把上会挂着一杆秤,来到草市巷旧粮食局附近找个摊位,摆好后,我就来回转着,看着各巷口出来拿着菜篮子的城里人。那时候的我也会情不自禁地吆喝着,虽然有时也很腼腆,但面对强有力的“对手”,比如河畔、呼台、南北关等生产队的卖菜专业户,就只能甘拜下风。
(图片来源于网络)首先你要行好价,先转着看看市场上同类菜水的卖家多少、优劣之差。有时候遇上好买家,赶在吃饭前就能卖完。在斤秤上,父亲经常教我们不能缺斤短两,秤杆高高的总能让买家称心满意。尤其是到了家家户户熬柿子酱的季节,会等来一个好主户,一纸箱西红柿都要了,这就要你送货上门,推着自行车在窄窄的头道圪洞行走,偶尔会看到一大户人家上百年的大门。进了院落,有熟悉的鸡冠花、月季花,还有早已洗好的葡萄糖瓶摆放在那里。过了秤,收了钱,也就十几块钱,有些时候买家嫌麻烦就找来一个相仿的纸箱子,和你一换。走出大门后,我会用力蹬着车,一边高兴地按着铃盖子,清脆的声音回荡在长长的小巷子里。
在暑假我会帮父母隔三差五到菜市摆摊子。依稀记得到了盛夏时,当时二哥在部队当兵,熟透了的西瓜全靠父亲大哥和我推着平板车在集市、在大街小巷、在玻璃厂附近摆摊卖瓜。让我多了种对父母亲辛勤劳动的理解,既锻炼了我与生活的融洽性,也成为我生命中很真实的记忆。
随着神木的经济发展,菜市场也换了好多地方。当时的菜市场除了草市巷粮食局附近,油库路上端那里,南斜街、炭市等等。那时候的摊位,经常会有工商、税务的工作人员,挨着过来收摊位的地皮税,少则一二毛,多则五毛,再后来,基本上是一块钱,看你占摊位大小收取税款。有时,一看见穿制服、戴大檐帽的过来,好多人会离开,或挑起装满物品的箩筐、推着平板车装模作样不卖了。
03.赶集摆摊儿记得是年以后吧,把妻子攒的一点私房钱在商贸大厦转租了化妆品摊位。不到一年,商贸大厦因一楼装修而即将撤摊,为了处理剩下的化妆品,我萌发了去店塔镇赶一回逢三逢八的集。妻子给我装好一蛇皮袋子的各式各样洗发水、洗面奶等,并且拿了些零花钱。我挤上了一辆去店塔的面包车,二十多公里路,走了四十来分钟,来到市场,我寻思着,化妆品应该离那些卖蔬菜等摊位远点,尽量靠近卖衣服、百货之类的摊点。铺开一块方方的大油布,摆好后,我就蹲在那里,看着不远处的农贸市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不多久,就看见一个工商所的,向我们这边走过来,大家都说还没有开市呢?免了吧。根本不顶事,每人掏了一块钱。这人刚离开,朝南的摊位上,又看见地方税务员过来收税,一边扯票据,一边喊着,你的税钱,一块。很不情愿地递给一块钱,还没有开市呢!也就在一瞬间,我发现左上衣兜里的十几块不见了,明明买票时还有,肯定是被人掏走了,猛一想,店塔车上那个中年人一直上车往身上靠,装着睡觉。一脸的无奈,我开始吆喝起来了,看见有人过来,就大声喊道:“商贸的化妆品,物美价廉,买一送一。”反正当时的那种勇气和胆量,到现在我才知道,那就是生活所迫而已吧。赶到太阳落山前,我开始收拾所剩不多的洗发水和其它零碎物品。这期间,吃了一顿二块钱的中午饭,没敢多喝水,毕竟一个人出来摆摊,不认识啥人,有些时候的确不方便。坐上回城的面包车,这次的钱藏得很严密,回家后,女儿拿着水果跑了过来,那一刻所有的疲惫、感悟悄然消失。家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再苦再累的过程,都能消化掉,就像在店塔摆摊的这段往事,只能在某一时间段再现,这也告诉我们的人生之路,注定要先苦后甜。
话说回来,摆摊也是一门学问,是一张推销自我的名片。除了体验、锻炼,最多的还是让茶余饭后的市民,有了梦的发源地。看着朋友圈、抖音、快手里到处都是摆摊设点的,而且是花样多多,创新创意,有种回到了从前的时光。年的疫情还不很乐观,低风险城市的我们,也要文明摆摊健康消费。当凤仪神木,共筑城市记忆成为当前最热衷的城市主题,越来越多的惠民摊位也将设置于迎宾广场、东兴广场、大兴游乐园以及鸟语花香的杏花滩公园,这一举措,暖了人心,火了生活。我的这段地摊记忆,注定会沉浸于人间烟火里,发酵、回味。文字
杭建新
意见建议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fdblog.net/zzxfg/111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