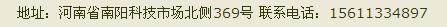古镇人物理发哑巴一
(一)
今天中午,我终于找到了马家哑巴的理发店。
在古镇上街,一处青砖灰瓦的房檐下,吊着一只八角形的红灯笼,暗红的木柱旁,挂着一块木板漆底的招牌,隶书繁体“马利平理发店”六个描金大字,显得古朴典雅。可美中不足的是,招牌上本应是毛发的“髮”,却写成了发财的“發”。不过,有招牌,总比没有招牌好,最起码,顾客不至于弄错。
我就曾经走错过一次,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冬天。
(二)
早在前几年,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闲谝,不知怎么就说到头发的事情了。一个说,这几年,理发店都不像理发店了。你看街上理发的,都是几绺子红头发的二毛子,要不就是留着长指甲、画的像鬼一样的暴露女。店里面音响震天动地鬼哭狼嚎的,从门口过都瘆的慌,哪里还敢进去剪头发。一个说,是啊,现在找个正经理发的太难了!给你剪几下子,然后揉一揉、吹一吹,回家一看,都不好意思再出门的。理发手艺不行,收钱却一点不含糊。哪里是理发,纯粹是瞎胡整。有个头发齐整的笑笑说,我给你们推荐个理发的,中街有个马家哑巴,只剪平头,我每次都在他那儿理,真心不错。
其实,我早就听说了马家哑巴的,还知道他的媳妇也是个哑巴——他的女儿曾在我校上学,漂亮机灵,各方面都很优秀,后来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一个特殊的家庭,能培养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让我羡慕敬佩。我还在想,三口人,两个不说话,一家人怎么交流哦。
听了同事的介绍,我心里一动,就有了见识哑巴的念想。
刚好那阵子头发长了,糟得人心慌。打听到哑巴的理发店在中街,于是在一个冬日的中,我独自一人前去古街寻找。
(三)
过街的路上,我在心里想象着哑巴的模样:苍老、木讷,走路重,指手画脚、哇哇乱叫?
记得小时候,上学路过河坝,总会遇到个蓬头垢面的男哑巴,丑陋猥琐,蛮力大,整天追着我们指手画脚,哇哇乱叫。我们也常常会远远地围着他,用石块投掷。但击中的少,倒是他脚步快,瞅准我们逮住一个,左手薅紧了臂膀,右手便曲了四指迎头迅击而来,任你怎么挣扎也避让不过。眼前瞬间一黑,接着金星四起,伸手一摸头顶,转眼长出几个“毛栗包”来,紧接着疼彻心扉,泪水情不自禁地就流出来了。疼痛的记忆,格外深刻和清晰。我家不远,还有一个女哑巴,人们都叫她“女瓜子”。邋里邋遢,衣服不辨布色,满是油污。老远都能看见白花花的虱子在她干枯的头发上爬来爬去。有太阳的冬天,就靠在人家墙角下,逮身上的虼蚤,掐的咯嘣响。常年乜斜着眼睛在路上游,传捡别家的剩饭剩菜吃,连猪食桶里的东西也不放过。见到她,大人们大老远就捂住了口鼻,匆匆而过。听大人说,女瓜子么娃,哪个娃儿不听话,会送给瓜子养,吓得我们乖乖的。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从小我便对哑巴很恐惧,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好感了。
(四)
穿过外街的车流,迎面有个巷道,连接着狭窄的里街。巷道两边,开着几个或阔或窄的门脸,装裱十字绣、打字复印、卖儿童玩具服装。如同这个季节一样,店里都很冷清,多不见店主,只有打字复印店里的女孩,坐在电脑前看手机,有人经过,也懒得张望。在即将进入里街的转弯处,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理发店门面。
店外没有招牌,门口有个蜂窝煤炉子,水壶在呼呼地冒着热气。房子不大,约十来个平方,天花板很低;屋里最显眼的是一把笨重的老式铁椅,地下围着扫拢的毛发;圈椅表面的白漆掉了不少,斑驳的铁锈散发出古旧的气息。靠墙放着一张三抽屉的黑条桌,上面堆满了推子、剪子、电吹风,还有洗发膏之类的瓶瓶罐罐,旁边站着钢筋拧成的脸盆架,最上端打着白毛巾。墙角,老式的彩电正放着古装电视剧。或许,这就是哑巴的理发店吧?
看见我走进来,一个坐在小板凳上看电视的小老头连忙站了起来,伸手指了指圈椅,示意我坐下。这老头不说话,头发花白、穿着老旧的蓝布中山装,应该是马家哑巴无疑了,我心里猜想着。于是也不言语,走到椅子前坐下,任由他给我系上围布,开始理发。
一阵剪子、推子的忙活,我的头发落了一地。忽然,“哑巴”开口说话了:洗哈吧?
我一惊:他不是哑巴?或许,哑巴只是一个绰号,实际上会说话?我疑惑着理完了发。我想趁给钱的时候,再跟“哑巴”说几句话,但他却去灌水了,我只好递给了一个忙前忙后的妇女——或者,她是“哑巴”的女人?(注:图片来自网络)(未完待续)
北京最权威白癜风专科医院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的专科医院转载请注明:http://www.fdblog.net/xfgpp/51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