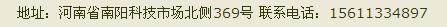创IP金庸诉此间的少年之辩辩辩
金庸老先生起诉《此间的少年》著作权侵权一案,据悉已经由广州天河法院受理。
吃瓜群众纷纷站队,迷妹们表示有“初恋和暗恋打起来你帮谁的错觉”。
而此案所涉及的同人文学侵权边界之法律界定,更是引起文学届和法律界两大阵营的激辩。目前法律界对此案的观点有几类:
侵权论,不侵权论,以及认为不侵权但构成不正当竞争论。
一、是否侵犯著作权
网评普遍把此案作为“中国同人文学著作权第一案”,认为此案结果会决定同人文学的整体定性,影响到这一文学形式的未来走向。笔者认为其实不尽然。
同人文学是否侵权还是要根据个案情况区分对待。本案的关键在于:
首先,《此间》所使用的金庸作品中的元素,属于思想还是独创性的表达;
其次,如果《此间》确实使用了金庸作品中的表达,这些表达是否具有独创性;
最后,即使前两个条件都成立,还要看《此间》的使用是否能构成合理使用。
思想还是表达?
《此间》的故事情节和文字表述和金作完全不同,其使用的金作中的元素仅为人物的名字、部分性格特征及部分人物背景和人物关系。
例如,根据百度百科对《此间》的人物简介:
郭靖:第五年入学,化学系,蒙古学生。属性是大哥,特点是身强力壮,服从组织和黄蓉,热心劳动,永远不缺乏活力。在宿舍中排行老大。爱好是蹦迪。
欧阳克:第五年入学,法律系,汴梁学生。属性是帅哥或者小白脸,特点是风流潇洒,很希望服从黄蓉却没有机会,极度厌恶劳动,永远备有充足的洗面奶和洗发膏和古龙水,永远领导黄蓉讨厌的那种服装潮流。宿舍号为,爱好是和女生说话,特长是国标舞和耍酷。
杨康:第五年入学,生物技术系(属于生物学院),汴梁学生。属性是懒虫,特点是很懒,比较聪明而不喜欢动脑子,比较会写东西而懒得动笔,眼睛位置生得稍微高了一点,总是看这个那个不顺眼。在宿舍中排行老三,爱好是睡懒觉,特长是和院长完颜鸿烈叫板。
以郭靖为例,郭靖与金作相符的要素仅为名字、蒙古背景(金作中郭也不是蒙古族,只是在蒙古长大),身强力壮,喜欢一个叫黄蓉的女孩子。其他特征,如年代,身份,大哥向,活力,爱好蹦迪等均与金作不尽相同。
欧阳克、杨康以及其他角色也是如此。
那么这些使用属于金作中的思想还是表达?
传统上认为表达是有形的而思想是无形的,但著作权法上的思想和表达早已突破了这种简单地区分。PaulGoldstein教授将现代著作权法上的“思想”和“表达”称为“区分作品中不受保护元素和受保护元素的一种隐喻(metaphor)”。
汉德法官曾经说过,“没人能在版权法所称的思想和表达之间确定一条固定的边界”。
角色及人物关系被他人使用多出现在续写作品中,而即使这类续写作品是否侵权也并没有定论。
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与他人续写作品《围城之后》的著作权侵权案中,版权行政部门认定后者构成侵权。而在四川方言剧《幸福的耳朵》第一季与《幸福的耳朵》第二季著作权侵权案中,一二审法院均认为不构成侵权。
说到这看官们可能都头大了。别忙,在笔者看来,这类案件的思想和表达并不难区分。
很简单,因为被诉作品已经一模一样地使用了原作中的人名!
“郭靖”、“杨康”、“欧阳克”,这些都是纯粹的表达,哪怕这些人名再短小,两个字也好,三个字也好,那也是原作中的有形的具体部分,而不是无形的抽象。至于这些人名受不受著作权保护,那是有没有独创性的问题,而不是区分思想和表达的问题。
纵观整个版权法的发展史,无论如何演变,无论思想和表达的定义变成何等的隐喻、何等的模糊,都只是纠结在无形的东西,即无形的东西抽象到何种程度变成思想。有形的东西始终都被保留在金字塔的最底层,确定是表达无疑。
至于人物的性格特征、背景和相互关系,应与人物的名字结合来看,而不是割裂开来。单独的思想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表达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琼瑶诉于正案判决中,法官就指出: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设置及人物关系,如果仅仅是‘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情侣关系’等,无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应属于思想范畴;如果就上述人物关系加以具体化:‘父亲是王爷而儿子是贝勒但两人并非真父子’,‘哥哥是偷换来的贝勒而弟弟是侧福晋的儿子’,‘情侣双方是因偷换孩子导致身份颠倒的两个特定人物’,则相对于前述人物关系设置而言,这样的具体设计无疑将处于金字塔结构的相对下层……”
《此间》中的人物性格、背景和关系虽然只与原作部分相同,但也是对这些人名的进一步限定。既然人名是表达,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也应该是表达。例如郭靖这个人名已经属于表达,那么蒙古背景、身强力壮、喜欢一个叫黄蓉的女孩子的郭靖,是对郭靖的进一步限定,因此只会使已有的表达更加具象,而不可能反而上升为思想。
由此可见,《此间》中使用的元素,属于金作中的表达,而不是思想。
2.有没有独创性?
当前的主流观点是单纯的角色名称一般不具有独创性。
在“我叫MT”游戏著作权侵权案中,北京知产法院对角色名称的独创性判断标准做出了阐释:
“对于名称、标题等词组或短语而言,判断其是否有创作性,应考虑其是否同时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该词组或短语是否存在作者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对于作者不具有选择与安排空间的词组或短语,因属于‘思想与表达的混合’,故不被认定有创作性。普通的或者常用的词组或短语,亦不具有独创性。
其二,该词组或短语能否相对完整地表达或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传达一定的信息。作品是作者思想情感的表达,是沟通作者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桥梁或纽带,一个词组或短语如果不能给予读者一个确切的意思,不应认定其有创作性。
具体至本案,对于‘我叫MT’这一动漫名称而言,因‘我叫......’这一表述方式是现有表述方式,而‘MT’亦属于常见的字母组合,因此,‘我叫MT’整体属于现有常用表达,并非涉案动漫作者独创,不具有独创性。
至于‘哀木涕’、‘傻馒’、‘劣人’、‘呆贼’、‘神棍德’五个人物名称,公众在不知晓原告游戏,而仅仅看到上述名称的情况下,显然无法对其所表达的含义有所认知。因此,上述名称并未表达较为完整的思想,未实现文字作品的基本功能。虽然公众在结合动漫《我叫MT》的情况下,足以知晓上述名称的含义,但这一认知已不仅仅来源于上述名称本身,而系来源于该动漫中的具体内容,这一情形不足以说明上述名称本身符合文字作品的创作性要求。”
以此标准来衡量,金作中的人物名字虽然经过取舍、选择、安排、设计,但也很难达到“相对完整地表达或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传达一定的信息”的标准。
但是,这些人物名字与其各自的性格、背景和关系相结合,则可能满足上述标准。《此间》中使用的这些性格、背景和关系虽然只是原作的一部分,但这些部分也可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物设计构思。
单独的名字“郭靖”是空虚的,但一个蒙古背景、身强力壮、喜欢一个叫黄蓉的女孩子的郭靖则基本呈现出了一个人物的轮廓。当然这个问题的判断也是非常模糊和主观的。可是《此间》中使用的并非单单一个人物,大概是大部分人物都存在这种情况,这样结合起来看,笔者认为很有可能已经达到独创性标准。
3.是否能构成合理使用?
虽然《此间》很可能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但笔者并不认为其构成侵权。
看到此案报道马上就联想到著作权法上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戏仿(parody)”作品是否侵权?之前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也跟陈凯歌闹了一阵子侵权之争,后来不了了之,都是这个问题。
中国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在美国法上戏仿作品是可能构成合理使用的。美国法认为戏仿是一种转换性使用(TransformativeUse),即不是以替代原作为目的,而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创作出新的表达和价值,实现完全不同的新功能。这种使用只要没超过一定限度就认为是合理使用。
比如google网页快照在美国是按转换性合理使用认定不构成侵权的。与《一个馒头》类似的讽刺戏谑作品,也都按是不是构成转换性合理使用来判断侵权与否。
美国法上的转换性使用,背后的理念是平衡言论自由和著作权保护。首先言论自由的保障是第一位的,真理越辩越明,除有违公共利益外,任何有利于丰富“思想和观点的自由市场”的行为都不应受到禁止。
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保护作者对作品的收益权,以鼓励创作,这就是著作权法的基石。平衡言论自由和著作权保护的两大工具,就是思想/表达二分法和合理使用。
转换性使用由于极富创作性,实现了新的功能,因此更靠近言论自由一方。
同时如果构成转换性使用,则并不会实质性影响原作的收益,那么对其给予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就降低了。
戏仿作品就是这类转换性使用的典型例子。
戏仿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替代原作或是制造混淆,他们对原作的模仿是大大方方的,如果人们看不出他模仿的是原作,反而是戏仿的失败。戏仿的目的或是为了讽刺批评,如《一个馒头》,或是为了借用原作产生一种特有的趣味或艺术效果,如《此间》。
人们会发现,如果你不允许他们借用原作的这些元素去戏仿,其他的讽刺、批评或创作方式没有办法给人同等深刻的印象,或者产生相同的评论效果或艺术效果。这种时候,这类表达方式具有唯一性,而大家知道,具有唯一性的东西都是不可垄断的。
当然,戏仿也不是无限制的。美国法上的经典案例北京去哪个医院看白癜风比较好北京哪治女性白癜风好
转载请注明:http://www.fdblog.net/xfgcf/8170.html